[编剧] 比利·怀尔德给编剧们的11条建议
2015-07-06 10:48:22
来源:豆瓣[摘要]比利·怀尔德给编剧们的11条建议:
1、观众是反复无常的。
2、抓住他们的喉咙,绝不要松手。
3、为你的主要人物设计一条清晰的行动线。
4、你要知道往哪发展。
5、你能把情节点隐藏的越巧妙越从容,你的编剧水平就越高。
6、如果你在第三幕遇到了麻烦,那真正的问题一定在第一幕。
7、来自刘别谦(著名导演)的建议:让观众自己去把2和2相加,他们就会永远爱你。
8、在做旁白时,要注意不要讲观众们已经看到的东西。要讲他们看不到的东西。
9、第二幕中发生的事情要能开启电影的结尾。
10、第三幕必须建筑在节奏和动作上,直到最后一个事件发生,然后……
11、……它就成了,不要犹豫不前。
采访全文
文:波菲里奥·罗伯特
注:聊天形式的访谈,文中对提问和回答未标注。
你起步于电影时,正逢一次大战之后,欧洲中心为一种焦虑所渗透。你在极端排犹主义文化环境中的犹太人身份背景,是否给了你一种阴暗的生活态度?
我认为这种阴暗观是美国式的。
在黑色电影中也是如此吗?
很多黑色电影都是流亡者拍摄的:你在欧洲时不但与西奥德马克(Siodmak)、乌尔默(Ulmer)、金尼曼(Zinnemann)合作过,还有弗立兹•朗格(Friz Lang)、奥托•普莱明格(Otto Preminger)…
普莱明格有那些黑色电影重要作品?
《劳拉》(Laura)、《人行道终点处》(Where the Sidewalk Ends)、《堕落天使》(Fallen Angel)…
我们谈论了马克思•莱因哈特、德国表现主义,以及寻找模式…
你看,你使用了一个关键概念:寻找模式。你一定要理解拍电影的人,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拍摄过各种不同类型电影的人,我们的作品风格是不同的。我不是拍一种电影,像希区柯克(Hitchcock)那样,或是米里尼(Minnelli),拍摄大型的都市音乐剧。作为电影导演,我对类型没有意识,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如此。我们并不知道“这部电影应该是这种类型的”。它是自发产生的,如同你的手写体一样。这是我看待它的方式、认同它的方式。如同我无法想象莫奈(Monet)在画风景时对自己说:“现在,等一下,我是一个印象主义画家,所以我必须这么画。”他没这么想,只是作画而已。当你观看电影时,你决定把一些相关联的理论加于它们身上。你或许会问我:“你记得你在1935年写的那部剧本吗?那个好人的动机是出于一种仁慈,这种情绪上的暗示又在其它四部电影中重复出现过。或者,你将摄影机置于……”我对这些毫无意识,我从来不这样思考。“我所有作品的大主题”,我说这个时总会笑出来。你尽己所能,试着去使一部电影足够好看,足够有娱乐性。如果你的作品中存在有某种风格的话,有识别能力的人定会将其分辨出来。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部希区柯克的作品,这是一部金·维多(King Vidor)的作品,这是一部卡普拉(Capra)的作品。你有自己的手写体,但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。
当你开始拍电影时,表现主义的风格对你有影响吗?你是不是看过大量德国表现主义绘画?
它是你的背景。柏林就是那样一座城市,如同置身于一部早期强盗片的拍摄现场。或许芝加哥在二、三十年代看起来也是如此。要知道这不是凯尔希纳(Kirchner)的发明。
到目前为止,每个接受我们采访的导演都有类似的说法。如果不是在有意识的创作,很难否认事实上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创作风格,犹如手写体,一种你看待事物的方式。
当然,否则你就是个管道工,一个流动工人。你是不由自主的,但是如果有五十个编剧、五十个导演,就会有五十种不同的处理方式。可以说有这样一个个戏剧化的问题:丈夫回到家,发现妻子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;那么,这五十个编剧和导演,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演绎手法,不同的讲述方式,不同的拍摄手法。在某些版本中,有些角色会成为谋杀犯,也许其它的版本会把三个人设计成以同床共枕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写的不一样,导演的不一样,感谢上帝。即使如此,导演的完成过程也是不容易的。就算你给十个导演相同的场景,相同的机位,相同的摄影师,拍出来的东西还是会不一样。
我看了1942年至1953期间的大量影片,它们很多都对我有所影响。《倒扣的王牌》(Ace in the Hole)令我印象深刻,我是与一位朋友一起看的,他现在是名警察。我们二十年未见,几个星期前恰好遇到。回忆往事时,我问他:“随便问一下,你还记得一部当时对我们特有影响的电影吗?”他说:“当然,《倒扣的王牌》,我刚重看了一遍。”
关于它的评论不多,不过它确是影响深远。那是一次大失败,狼狈不堪,他们把名字改成了《大狂欢节》(The Big Carnival)。它没有成功。你知道,我不是一辈子都在对自己说,这部电影不成功,是因为它走在时代的前面。这部电影不成功是因为盖瑞·库柏(Gary Cooper),我应该用加里·格兰特(Cary Grant)。我不想这些。我只是说算了吧。它不成功,我也没写好、没导演好,演员没用好。忘记它吧。我没有8mm、16mm版本,我没有阅读老剧本,当我的电影在电视上播放时,我也毫不在乎。太无聊了。现在你问下个问题吧。
我们可以识别一种存在于四十年代电影中的视觉风格,一种与明暗对比法、深焦距、低凋灯光有关的视觉风格,一种黑色情绪。
当然,你会说《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》(Caligari)是一部黑色电影。我也可以认为《俄底普斯》是一部黑色戏剧,对吗?
同样,George Simenon写了很多你所谓的“浪漫黑色小说(roman noir)”。我认为左拉(Zola)同也有许多那种黑色元素。问题在于,最后你是否有一种精神释放。举个例子,你会吧金·维多的《Crowd》归于哪一类?它是“自然主义”的作品,还是黑色电影?
当然是自然主义,或许有些美国表现主义的成分。
给我一个黑色电影的经典例子。
《双重赔偿》(Double Indemnity)。
可能电影主题是有关于死亡和绝望的。《Spiral Staircase》是黑色电影吗?当然是。虽然相对于罗伯特·西奥德马克其他黑色电影来说,它更歌特派(Gothic)一些。和你不同,他在黑色电影之外并不太成功。恩,我知道你们不会与罗伯特·西奥德马克讨论这个问题,因为他已经不幸逝世了。早在美国人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之前,你和西奥德马克都已经在黑色电影中广泛使用了实景拍摄。是的。一旦你厌倦了派拉蒙片场的纽约街景,或者是华纳兄弟片场的置景、以及Metro制片场的火车站之后,你就会想要做得更好、更大,你就会走出去完成它。但是,让我们抛开黑色电影说一会儿,我们走出摄影棚所做的这一切,是因为我们不能再轻易地愚弄观众了,因为观众已经通过电视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。他们全都知道,你不可能再欺骗他们。
你认为观众自身的态度在战争后有所改变吗?
观众改变了。他们变得更聪明、智慧、更难把握,更挑剔,不只是难以给他们娱乐性,而是更难让他们去电影院。我们这些电影人突然开始要竞争,与那些可以在家里轻易观看的东西竞争。他们甚至不必出门、停车,在嚼爆米花的时候给入室打劫者一点可乘之机。现在非常困难去克服……那个词是什么?
无序状态(entropy)?
对,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?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少。制片厂曾经每年拍三百、四百、五百部电影,现在只有八十部。在这八十部之中,有六部可以是似乎每个人都会去看的大片,其它的就被半途而废了。那些想看不同电影的观众会失望的。
在你的作品中,《双重赔偿》、《日落大道》(Sunset Boulevard)、《倒扣的王牌》,以及我认为至少某部分的《失去的周末》,它们显而易见是黑色电影。
但它们是一组形态各异的作品。我希望我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。重复自己是无聊的,我在当记者时就明白这一点。我们没有特意去拍某种风格的电影。
这些背景、风格、或第二次世界大战,对《双重赔偿》有影响吗?
它是詹姆斯·M·凯恩(James M.Cain)的一个短篇小说。我并没有补充任何焦虑、忧虑,或任何纳粹迫害情绪。雷蒙德·钱德勒(Raymond Chandler)和我在做剧本时,只是想让它戏剧化一些,只是强调凯恩先生的想法。诚实地说,我不能指出这些影片有任何细节反映了我的背景或者我的来源。也许我没有意识到,或许我已经足够美国化了。我们现在讨论的可能只是时尚,一种普遍现象。样式改变了:窄领带变宽,宽裤腿变窄了。一些里程碑式的导演,——我不认为自己是他们其中一员——当他们建立一种标志时,比如D·W·格里菲斯(D.W.Griffith)的电影,金·维多的《Crowd》,茂瑙(Murnau)的《最后一笑》(The Last Laugh),刘别谦(Lubitch)的所有电影,人们观看他们的电影并且受到影响。
关于影响和风格的问题,我们采访了爱德华·迪麦德雷克(Edward Dmytryk),请问他在《谋杀,亲爱的》(Murder,My Sweet)中是否有意识地建立了一种风格,他就此谈了一些。有没有任何特别的作家或者导演影响过你? 有两个人,我与他们都合作过。一位是刘别谦,我做编剧时与他有过合作;还有一位我是以导演身份与他合作的,我是说他出演了我的一些电影,Erich von Stroheim,不过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混合,因为你无法找出比他们俩更相反的另外两个人了。
人工技术和超级现实。
是的,不过是在可能的最高层次上的人工技术。我是说,我肯定你知道刘别谦的去世对世界和电影工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到象刘别谦那样。他把秘密带进了坟墓;他做到了。Stroheim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如果你能想象的话,这就说明了我不是一个风格统一的电影导演。
不过总有原因使你选择那个素材。比如说,为什么你选择了《双重赔偿》这样一个故事?为什么你选择与钱德勒合作?
啊,这是一个好问题,我敢肯定你知道我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,并写了下来。所以我会给你一个很浪漫的解释版本。一个制片人,(Joe Sistrom),对我说:“你知道詹姆斯·M·凯恩先生吗?”我说:“当然啦,他写了《邮差总按两遍铃》(Postman Alwaye Rings Twice)。”他说:“我们没有那个小说,它是Metro制片场的;不过为了赚钱,他又写了一个《双重赔偿》,连载于老版的《自由》杂志(Liberty Magazine)上。你看看吧。”所以我就看了,我说:“真不错,虽然不及《邮差总按两遍铃》,我们还是来做吧!”于是我们就买下了它的版权。我们问:“凯恩先生,你愿意与怀尔德先生一起合作写剧本吗?”他说:“当然愿意,不过不行,我正在Twentieth Century-Fox公司给弗立兹·朗格写《Western Union》。”制片人于是说:“好莱坞有一个写《Black Mask》的神秘作家叫雷蒙德·钱德勒。”当时还真没人知道他。于是我们一致同意:“让他加入。”他当时还没有在制片场内工作过,接着他就开始了。你要知道我并不是辗转反侧,把事情安排到最后一个细节,不像歌德(Goethe)构思在艺术那样,不是的。我们找到钱德勒是个偶然。我说我喜欢这个故事,谁来跟我一起写,噢他很忙,还有一个写侦探故事的人……当然结果是很好的,被(奥斯卡)提名了。这都是没有预料的。可能有点象制作香水一样,时好时坏。这边加点香精,那边再加点什么,做出来的味道不是玫瑰花香就是屎臭,完全是自由的。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开始的,没有什么诀窍。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我如何选演员,如何组织剧组成员,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做得最好。不过萌芽总是那么的简单和戏剧化。
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,你确实捕捉到了黑色电影的氛围,尤其是美国加州标志的那一种。
是这样的,一开始你希望你的作品能奏效。但有时它不是这样的。有时它就像个煎饼一样平淡。即使你是最出色的画家,你画了一幅伟大的油画,可以送去卢浮宫了,当你画下一幅的时候又没戏了。所以你就把这该死的画扔到去火里烧,对吧?因为画布只有两美元十一美分的成本。你拍了电影的四分之三时,你知道它将是一部垃圾,这可比两美元十一美分要贵多了。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它无法协调,无法成功,无法奏效,不该发行。我们发明的这架该死的飞机飞不起来,它要坠毁了。不过你已经投资了两百、三百、五百万美元或更多,你不能就这么把它扔到垃圾桶里。你尽了最大努力,然后发行的时候,你羞愧地作在一旁。我们无法把我们的失败掩埋起来。它们真的会继续发臭。好莱坞没有不失败的人,绝对没有每次都成功的人。看看萧伯纳(George Bernard Shaw)的所有作品,你能记住他的六部戏剧。不过他还有四十部作品不成功。四十部。
关于《双重赔偿》,你最后决定毒气室段落是反高潮的?
最初我们挺喜欢这场戏。弗瑞德·麦克默瑞(Fred MacMurry)喜欢它。开始他并不想演,没有那个主角想演这种戏。不过后来他非常愿意。我拍《公寓》(Apartment)时与他再次合作。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,不过可以告诉你,当他拍这场戏时,没有犹豫,什么都没有,他的表演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拍完了整场毒气室死刑执行的戏,一切都极为精确而平稳。然后我意识到,这场戏已经结束了。在办公室外那场戏中,纳夫(Neff)瘫倒在去电梯间的路上,点香烟的力气都没有了;我已经在那里给出了结束语。例如,你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警笛声,或是救护车,或是警车,你知道这已然结束了,不需要什么毒气室。小说中麦克默瑞和罗宾逊(Robinson)之间那种父子情,或者情感关系是精心处理过的,不仅仅只是香烟打火机。我尝试过那样处理,也完全了解美国电影中伟大爱情故事不是克拉克·盖博(Clark Gable)和费雯丽(Vivien Leigh),也不是琼·克劳弗(Joan Crawford)和拉娜·透纳(Lana Turner),而是克拉克·盖博和斯宾塞·倔西(Spencer Tracy)。你想做出那种感觉,我也知道它可以成功。我是对的,不过我也可能错了。
麦克默瑞是一个理想的扮演者,他的角色是个浪漫的揭露者,外表足够刚硬,又足够软弱到被女人引诱。钱德勒说他觉得阿兰·拉德(Alan Ladd)是个小男孩式的硬汉。他只是一个中产阶级推销员。如果他足够坚强,那就没斯万克(Stanwyck)什么事儿了。他必须在整个事件中被诱惑,被利用。他是一个突然变成谋杀犯的普通人。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阴暗面,一个普通人如何沦落成为一个凶手。不过寻找主角是困难的。每个人都拒绝我。我来来回回地找,相信我,包括乔治·华特(George Raft)都被考虑在内。没人愿意演,他们不想演这个冷漠的男人。最初麦克默瑞的可能性也很小。他说:“你看,我是个吹萨克斯管的。我和克劳德特·克拉伯特(Claudette Colbert)一起拍喜剧片,你要我做什么?”“你总要走出第一步,相信我,会有回报的,并没有那么难。”所以他演了。不过他并不想这样做,他不想被杀,也不想去做杀人犯。斯万克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。迪克·包尔(Dick Power),他自愿出演。他告诉我:“我愿意无偿地来演。”他知道这是从那些无聊的事情中脱身的方法——你知道他要对着茹比·克勒(Ruby Keeler)脸演唱,他想从中摆脱出来,所以他想死了要演(纳夫)。那是在《谋杀,我亲爱的》(Mueder,My Sweet)之前。他来我办公室对我说:“看在上帝的份上,让我演吧。”“你看,我能用个喜剧演员,就这么拍了。不过我可不想用个歌手。”他在《谋杀,我亲爱的》中演得非常棒。这种中产阶级的阴暗面,是否正是钱德勒所描述的情境,当温顺的家庭主妇们盯着她们丈夫的脖子看时,她们感觉到的是刀刃?
而你在《公寓》中的处理只是有点玩世不恭。
钱德勒比我更玩世不恭,因为他比我浪漫多了。他有自己的古怪原则,认为好莱坞就是一堆冒牌货。我不能说他全错,但他确实不完全了解电影,以及电影的成功方式。他不能结构一部电影,小说已经够为难他了。不过他的台词非常精彩。我为此受了不少罪。在跟他和他的臭烟斗待了几个星期之后,我自己也能吐出几句好的台词来了。我们把他留在拍摄现场,随时讨论修改对白。
我在写《公寓》初稿时就已经超越了钱德勒的技巧,影响我的有两件事情。首先自然是《Crowd》,那个想从按部就班的大集体中脱离出来的家伙。我最初也为大卫·里恩(David Lean)电影《Brief Encounter》中尼奥·克沃德(Noel Coward)的一场独角戏所吸引。我后来告戒自己,有趣的人物不是这个男人和一个有夫之妇的纠缠,而是他用谁的公寓来偷情,他是个回家找寻温暖被窝的可悲男人。
作为剧作家,钱德勒再也没能达到《双重赔偿》同样的成功,《蓝色大丽菊》(Blue Dahlia)为他获得了又一次奥斯卡提名,不过票房和评论都不成功。
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奇怪的人,一个真正的怪人。他曾经是个酒鬼,而且非常恨我。他不习惯遵循这条纪律,每天早上,不管有没有情绪,你都不能等待缪斯来亲吻你,只能写。他对我恨之入骨。当我结束跟他的合作时,我想他又开始偷着喝酒了。我逼得他又喝起酒来。那次我们唯一的一次合作。他绝对是一个聪明的人,非常智慧。
你说钱德勒写对白有一套,不过编情节……
他的情节很糟糕,不过情节糟糕才不会防碍气氛。《唐人街》的情节不好,罗斯·麦克唐纳(Ross MacDonald)和达什·哈默特(Dash Hammet)的大部分小说的情节也不好。不是情节,是屋里的气氛,是对一个耳毛长得可以抓住飞蛾的男人的描述,是这种东西。
有意思的是,钱德勒可以提供很好的影像、画面,而我可以提供一种“钱德勒主义” (Chandlerim)式的东西。这很奇怪,你知道,事情总是这样产生的。他不是年轻人了,在我们为《双重赔偿》一起工作的十个、或者十二个星期期间,他就没有学到点……技巧。接下来他就自立了,约翰·霍斯曼(John Houseman)几乎没有盯着他写。剧作家是个流浪诗人、三流戏剧家、半个工程师。你要建构一座桥,它要承担交通,其它的一切,戏剧和表演都在此发生。当然,编剧是技巧和一点文学天赋的结合,也是一种如何去控制的能力,这样观众才不会睡着。你既不能让演员厌倦,也不能让观众厌倦。
钱德勒的经历似乎是好莱坞小说家中的一个典型,如纳撒尼尔·威斯特(Nathaniel West),福克纳(Faulkner)……
钱德勒从来不以戏剧化方式思考剧本,所以他做不好。
我记得在派拉蒙的时候,每天下午都要和斯各特·菲司杰瑞德(Scott Fitzgerald)一起喝咖啡。要知道他是筋疲力尽,失望至极。而且许多这样的小说家都带着一种嘲笑在做电影。我年轻时候,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神圣的事情。我想,上帝啊,这太棒了;我在写剧本,这就是我的生命。他们只是做了(为了赚钱)而已。这不是他们的最爱,就像是跟一个五十美分的妓女做爱一样。那些制片厂里的白痴给了他们这么多钱,却没有给他们指引方向。我们拍电影的人,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,我们流血、我们痛哭、我们舞蹈,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
你是否在《失去的周末》的作者角色中加入了一点钱德勒的影子?
一点也没有。或许有点下意识的影响,不过当时很多作家都酗酒。查尔斯·杰克逊(Charles Jackson)小说给我的感觉是这个角色太无情了。然后我开始研究,与酒鬼、医生们交谈;我意识到小说并没有夸张。在好莱坞,酒鬼是可笑的,就像W·C·菲尔茨(W.C.Fields)那样。不过我知道,如果我能表现一个不可笑的酒鬼,能够深入表层之下,它就会是一部好电影。 选择雷·米兰德(Ray Milland)是以选用麦克默瑞的同样模式吗?不完全是。我想要何斯·弗瑞尔(Jose Ferrer)。我刚读完小说就在百老汇看了他的演出。但是制片厂想要一个英俊一点的男主角来减少一些冷酷感;这是成功的。雷·米兰德(Ray Milland)永远也得不到奥斯卡,如果他没演那个酒鬼……我不知道为何如此,五年后,或者再晚点,简·威曼(Jane Wyman)在她的电影(《Johnny Belinda》)中也是这样;如果你不能说话,不能走路,如果你的角色是个神经质,别人就会认为这是伟大的演技。
我们能再谈谈《倒扣的王牌》吗?我提到我看的时候还是个小孩,它对于一些人如何利用他者悲剧的描写使我非常难受。
我们的主角,那个记者,是科克·道格拉斯(Kirk Douglas)扮演的。他当时停止拍片,希望有一个好故事能使他重新回到辉煌,回到那个大市场之中。他想起了弗洛伊德·科林(Floyd Collins)的故事。他们写了一首歌,卖着热狗,还有一个马戏团,差不多是马戏团,人们都来看。因为那部电影我被所有的报纸批评。他们非常不喜欢它,他们说太玩世不恭了。去他妈的玩世不恭。我告诉你,你读到有架飞机在附近失事的消息,你想去现场看看,却根本进不去,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在那里捡垃圾,那些偷死魂的人。我记得看完那些关于《倒扣的王牌》的可怕的评论后,我来到Wilshire 大街,那里有一起车祸。有人被撞伤了,我停下车,想要去帮助那个撞伤的人。这时有一个人跳下车就拍照。我说:“你最好去叫辆救护车来。”“去他妈的叫医生。我得去《落杉矶时报》,我拍到了照片,我得走了。我在这里只是拍照片,我得把它送过去。”如果你将这一幕在电影中表现出来,评论家们就会说你是在夸张。
《倒扣的王牌》之后你脱离了传统黑色电影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点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,例如《热情似火》(Some Like It Hot)、《吻我,傻瓜》(Kiss Me,Stupid)。这个转折有没有什么原因?
没有,我不知道。如果当时有人给我《驱魔人》(The Exorcist),我会马上把它拍出来。如果现在有人给我《Waiting for Mr.Goodbar》,它是一个镇静剂,我也会马上完成它。如果有你所说的黑色的东西激发了我,比如有精彩对白的故事——我正在筹备一、两个这样的东西——而且已经有了成型的剧本,我就会去拍。这不是说:“我以后再也不穿脱下的衣服了。”不是的,事情就是这样的。
《双重赔偿》引发了一大批第一人称叙述的电影,你是否看到了四十年代的这种趋势?
我一直就是非常善于叙事的人,并非因为叙事是一个懒惰者的支柱。也许是这样的,不过要做好叙事并不容易。比方说,我在《日落大道》中的设计,让死人来做叙事者是一个有效的讲述故事的方式;两句话就可以实现需要20分钟来戏剧处理和拍摄的东西。很多人都在尝试叙事,不过他们不太懂技巧。很多时候的错误是,他们都在旁白中告诉你一些你已经看到的东西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不过如果它有所添加,能带来新东西、另一种角度,那也不错。
你如何看待评论?
读那些关于我的任何东西都让我感觉尴尬,就是让我尴尬。我喜欢的是表述……相信我,相对于一篇好评论或是一本书对我的认可,我更喜欢来自一个像阿加莎·克里斯蒂(Agatha Christie)这重作家的恭维,她说她的小说改编电影的唯一成功是《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》。这会让我很高兴。还有就是关于《双重赔偿》,凯恩先生对我们说:“嘿,听着,电影可比我的短篇小说好。”
在美国很多评论推崇作者论。你当然可能知道,《美国电影》(The American Cinema )杂志的沙瑞斯先生(Sarris)对你的评价可能不够高。
恩,有人必须忍受安德鲁·沙瑞斯先生。他没把我放到他的“A”级名单里,我不觉得失望。让我告诉你,有件事比被忽略更让我痛恨,那就是言过其实。对我来说这并不太重要。你知道这些事情的趋势,以《纽约时报》为例,在一年之内你可以从十佳电影落到百部最差电影中去。就是这么迅速和下跌,它随时可能发生。我记得有一年,沙瑞斯说最佳影片是查理·卓别林的《香港女伯爵》(Countess from Hong Kong)——那是一部绝对恶心的电影。我当然不是否认卓别林曾经是最伟大的。如果沙瑞斯说我们别提它了,或者说米开朗基罗(Michelangelo)晚期作品价值比较次要、有点惭愧,但并不漠视他过去的作品。他说这些就好了,但是《香港女伯爵》的确不是那一年的最佳影片。太荒唐、太糟糕了。所以我对作者论不是太在意,也对宝琳·凯尔(Pauline Kael)写的那些垃圾不在意。我的意思是,我认为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(Last Tango in Parris)是好电影,我写上一页半篇幅的评论,但决不是十二页!要进行电影制作的变革吗?贝尔特鲁奇(Bertolucci)是当今的出色导演;但是,看在上帝的份上,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不是她所认为基督再世。《纳什威尔》(Nashville)亦是如此;一页又一页地写,她是在强加读解。要不就是将一部策划很好的电影烘烤一番。举个例子,让我们来谈谈《大白鲨》(Jaws)吧,它的制作是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。它是为了营销而制作的,而且非常成功。斯皮尔伯格先生当时年轻又聪明,他从来没想过要它成为《战舰波将金号》(Battleship Potemkin)。他没想过,只是拍了《大白鲨》,一个惊悚片。如果他吓住了观众,让他们感到害怕了,他就达到目的了。就像有人做了一套很好的餐具,想在五美分、十美分店中做营销,而不是在卡地亚(Cartier)的连锁店。没有人假装它会在国会图书馆被展示,以及它会成为一部经典。不过这对于凯尔女士是不够的。我们的本土评论家,查尔斯·夏普林(Charles Champlin)很聪明,很不错。不过你看一眼他写的评论,他说从现在开始一百年之内人们还将会讨论《香波》(Shampoo),可是十天之后人们就不再讨论它了。从现在开始一百年?他在说什么?
我刚读过洛特·艾斯纳(Lotte Eisner)的《Haunted Screen》。她定义了“影调”(stimmung),她说那是通过灵魂的共鸣所传递的一种情绪。它是一种氛围:“通常弥漫着一种神秘和忧郁的自然外景,或者是有一屡透过窗户的街灯、油灯或者阳光的室内景。”你认为是你的电影引起了这些反应吗?
是的。它们呼应了这种“影调”。不过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影调。你可以有一种非常愉悦和浪漫的影调,艾薇拉·玛蒂根(Elvira Madigan)就是一部充满了美好影调的成功电影,它比任何其它影片有更多的氛围。还有大卫·里恩的所有电影,比如《伟大前程》(Great Expectations),它充满影调,不是吗?这种影调在《双重赔偿》中,就是那种对加州房屋、那些家具和一切东西的感觉,阳光照进满是灰尘屋里;空气中漂浮着灰尘,她是个坏妻子,对女儿毫不关心。我也尝试把这种影调用于《日落大道》中斯万森(Swanson)的家中。我当然也计划了就《日落大道》的黑色元素对你进行采访。如果没记错的话,对于房屋的描述是有关于威尔斯·拜瑞(Wallace Beery),她曾经嫁给过他。你知道,最初的想法是把它拍成喜剧。我们想请梅·韦斯特(Mae West),她拒绝了。然后派拉蒙请歌劳瑞亚·斯万森(Gloria Swanson)试镜,她几乎被淘汰。你知道,斯万森具有许多诺玛这个角色的素质了。拍《日落大道》期间对影调最大的威胁是我们失去了原定男演员(Montgomery Clift),换上比尔·侯顿(Bill Holder)之时。他比我们想要的年龄要老一些,斯万森不想把自己化妆成六十岁。不管怎样都有问题。这是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用尽伎俩的女人;谁知道一个年轻演员,至少是看起来年轻些的演员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。
你是怎么请到西西里·B·德米里(Cecil B. De Mille)在影片中扮演他自己的?
制片厂总裁(Henry Ginsberg)可不能像命令侯顿那样命令他。需要做的只是请求他,并且为他一天的拍摄工作每天付出一大笔钱(一万美金)。
在《双重赔偿》和《日落大道》中,你使用了同一个摄影师约翰·塞斯(John Seitz)来为那些抑郁的内景做灯光设计。
约翰尼·塞斯是个伟大的摄影师。他无所畏惧,他应该凭《Five Graves》拿奥斯卡奖,我以为他肯定能凭《日落大道》获奖。
《双重赔偿》的最后一场室内戏……
是的,很不错。
还有外景的夜色,铁轨闪闪发亮。
约翰尼是优秀的。
湿漉街道,这是另一种好的影调手法吗?
是的,不过随后它就变成俗套了,你知道。
下雨的确能引发伤感。
伤感,当然了。雨比雪便宜点,也没雪看起来那么假。雨很好,雨伞也很好,雨伞下的谋杀,希区柯克在《in Foreign Correspondent》中这样做过。非常、非常好。在《双重赔偿》中,芭芭拉·斯万克的化妆……那是个错误,大错特错。为什么?我不知道,我希望她是金发,金发女郎更有趣一些,不过……
她的头发看起来很冰冷。
是的,我希望让她看上去那样。但你必须明白一点,这是个错误。拍完之后,我第一个发现这个错误。我在跟人讨论乔治·斯蒂文(George Steven)的《郎心如铁》(Place in The Sun),我认为那是一部杰作。不过那人说:“是部好电影,不过有个低俗的符号使它几乎不值得成为杰作,就是那个律师,他是个瘸子。一种正义的缺陷,有一个拐杖。这是一种庸俗和过时的东西。”
“恩,我同意。事实上斯蒂文也同意你的看法。”不过要知道,如果是演舞台剧,第三场演出后你到后台跟演员说:“明天不用拐杖了,好吧,明天去掉拐杖。”可是电影已经完成了一半,已经拍了四个星期斯万克的戏,我才发现犯了一个错误。我不能说:“明天别戴那顶金色假发了。”我被卡住了……我不能重拍四个星期的戏,完全被卡在那了。我责备自己,错误发现的太晚了。幸运的是它没有影响到影片。不过假发太厚,我们对做假发还不太聪明。不过当人们说:“天哪,那个假发,看起来也太假了”,我回答:“你注意到啦?那是我有意设计的。我需要这个女人身上的虚假,品味低俗,假头套。”这就是我从中摆脱的方式。
人物简介:
虽然在1944(《双重赔偿》)到1951(《倒扣的王牌》)的七年之间,导演-编剧比利·怀尔德只拍了七部黑色电影风格的影片,但他毫无疑问是经典黑色电影时期的种子导演。怀尔德1906年6月22日出生于维也纳,取名萨缪·怀尔德(Samuel Wilder)。怀尔德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,他从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学院辍学,当了一名记者。1926年,他移居柏林,并在一家大型娱乐报纸做犯罪报道记者。1929年,他和西奥德马克兄弟、艾格·乌尔默、弗瑞德·金尼曼——他们都很快脱离纳粹统治流亡到了好莱坞——合作了Mennschen am Sonntag,一部由尤根·彻夫坦(Eugen Schufftan)摄影的短片,并在UFA公司开始了编剧职业。作为一个犹太人,希特勒的上台迫使他逃离,1933年先是到了巴黎,在那里联合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《Mauvaise Graine》;然后去了墨西哥,在那里等待进入美国的签证,并最终抵达洛杉矶。怀尔德的母亲和没有逃离的其他家庭成员最终都死于集中营。虽然英语能力有限,怀尔德还是受聘于哥伦比亚、二十一世纪福克斯剧本部,随后在派拉蒙公司,他和查尔斯·布莱西特联合,为欧内斯特?刘别谦和霍华德·霍克斯等著名导演写剧本。
像普雷斯顿·斯特奇斯(Preston Sturges)一样,怀尔德对于其他派拉蒙签约导演对他剧本的改动不满意,并争取自己做导演的机会。从1942年的《主要的和次要的》(The Major and the Minor)开始,怀尔德成为了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。与雷蒙德·钱德勒联合编剧的电影《双重赔偿》是他的第一部黑色电影,它们都带有愤世嫉俗和黑色幽默的风格。尽管他后期拍摄的作品大多是喜剧片,他的黑色电影被认为是从战后法国开始至今的这一流派电影的原形。1978年怀尔德宣布引退,一直居住于洛杉矶,2002年逝世。
怀尔德黑色电影作品包括:
《双重赔偿》Double Indemnity(1944)
《失去的周末》The Lost Weekend (1945)
《日落大道》Sunset Boulevard (1950)
《倒扣的王牌》Ace in the Hole (同《大狂欢节》,The Big Carnival)(1951)
合作方动态
-
 人民网人民网,创办于1997年1月1日,是世界十大...
人民网人民网,创办于1997年1月1日,是世界十大... -
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以宣传电影、培养电影观众、传播影视文化...
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以宣传电影、培养电影观众、传播影视文化... -
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“幸福蓝海国际影城”是幸福蓝...
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“幸福蓝海国际影城”是幸福蓝... -
 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都市情感话题剧《想明白了在结婚》目...
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都市情感话题剧《想明白了在结婚》目... -
 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巨资打造的电视剧《楚汉争雄》,由黄秋生...
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巨资打造的电视剧《楚汉争雄》,由黄秋生... -
 中视丰德影视版权公司中视丰德影视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北...
中视丰德影视版权公司中视丰德影视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北... -
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由唐德影视斥资重磅打造的战争钜制《彼岸...
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由唐德影视斥资重磅打造的战争钜制《彼岸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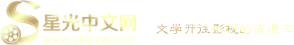

 分享
分享



 客服QQ:1055000316
客服QQ:1055000316